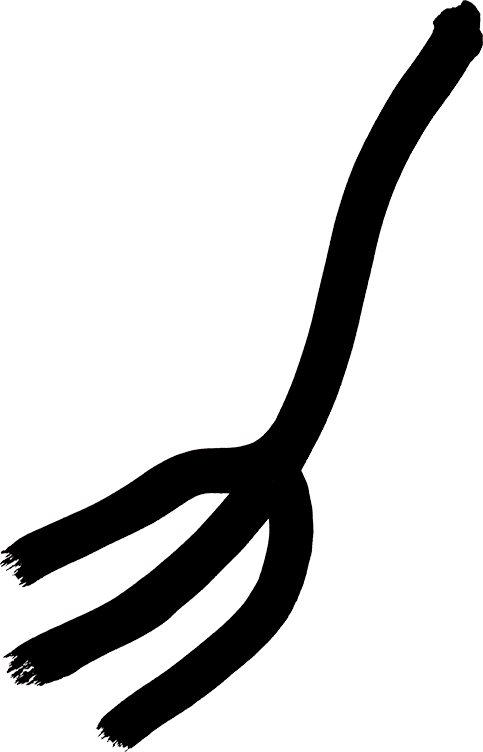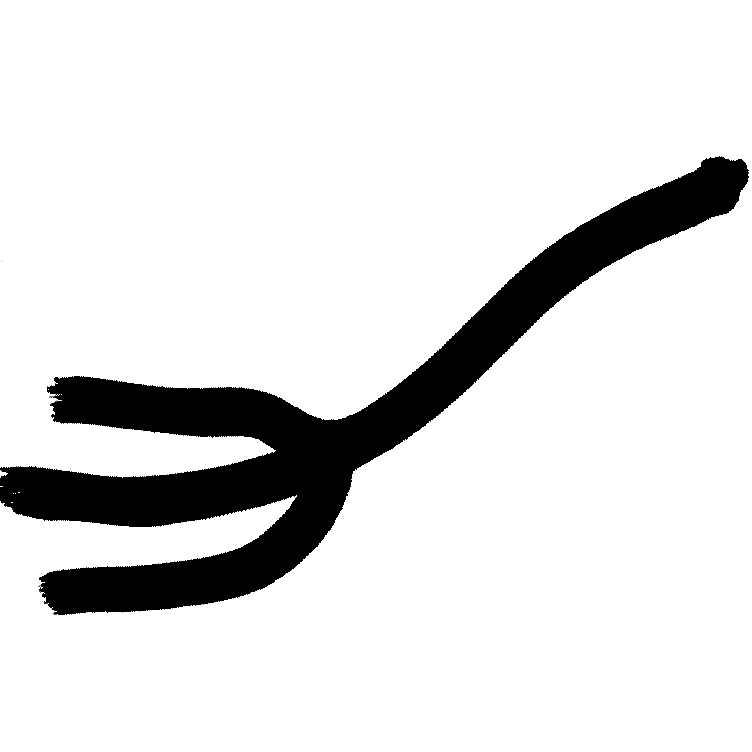22 Nov 山中廢墟的雨夜

村莊廢墟上長出的樹,正對著我的窗。「阿爾卑斯」系列,2014年
此刻我行走在阿爾卑斯山的艾坎山區(Ecrins),在香索(Champsaur)和香坡隆(Champoléon)兩個山村之間的路上,渾身濕透了。
早上的時候,我出發準備走二十五公里的路,翻兩座山去香坡隆的朋友家。剛收拾好背包離開山村,就看見西南邊的烏雲緊緊地壓著高山,已經向地面瘋狂地拉下細長又柔韌的烏絲,我怔在那兒看著,轟隆一聲暴雷就打了下來。眼前是個岔道,蹲下來攤開地圖,空氣中盡是風雨的氣息,我分明地感覺到地圖在手中越來越濕潤,好像再一會兒工夫就能軟成一攤泥水。正幻想著,一大塊冰雹就砸在了地圖上。
我在風中邊疊著地圖邊跑回村子裡。站在一個屋簷下看一串串珠簾無止境地下落,我陷入了猶豫,不知是否該冒這個險獨自在大雨中翻兩座從未去過的高山。天氣預報顯示一整天都可能下雨,但山中陰晴不定,眼前這麼大的冰雹過後,或許只是一些微不足道的細雨罷了。地圖上標示這半山中有兩個小木屋,分別在五公里和十五公里處,心想,若是無法翻越兩座山,至少我可以在山裡的木屋裏面過夜,等待天明再作打算。
中午的時候,天空總算放出了一條晴朗的罅隙,我二話不說就背上包又出發了。一個多小時之後,我穿出森林,在半山腰中看到了一小片平地,靠著山坡有一間房子,這就是地圖上標示的第一個森林木屋。走近前才發現,這是一個普通的農舍,遠非給行人歇腳的那種小小的木頭房子。屋子本身是石頭建造的,側邊塌成一片廢墟,屋前是一塊平整的地面,還看得見石頭砌成的地基。此處,與對面的高山仿佛觸手可及,但眼前的深谷又讓人一眼看不見底。先前在山下的某一塊告示牌上了解到,這山中零星散落著一些村舍,眼前的這一小塊,大概就是前人在山林中開闢的空地,在此建起過一個三五戶人家的小村落。但在一個世紀以前,人們紛紛下山,村落就成了廢墟,只剩下眼前這個半倒塌的屋子,應是幾番修葺,為登山者留著。屋前的坦地相當大,我眼前浮現出人們在晾曬穀物或者宰殺獵物的場景。靠近山崖的地方,視野最為蜿蜒深邃,後人在那放置了歇腳的木頭桌子和長椅,它的不遠處還有一樁鑿空的樹幹當做水池,接著突突突的從屋背後溪谷引來的清泉。雨後,這清澈冰涼的山谷水流得更加迫不及待了。
我徑直走向山崖邊的桌椅,此時整個山谷都是我的。掏出麵包啤酒和本子,一邊吃一邊看著遠處的山嶺。峽谷漸漸抬升,蜿蜒處聳立著幾座白雪皚皚的山峰,要往前趕路,就得從那山峰之間的某個埡口翻過去吧。我忽然覺得路途是多麼遙遠啊,假如我住在這個村子,或許一輩子都沒有理由要去翻那座山。眼下天空還有一些晴朗,然而山谷的出口那邊,雲雨已然籠罩了群山。樹枝搖曳,我感到一場大雨分明已在身後襲來。
推開屋子的兩扇早已被歲月撫去了稜角的木門,只聽得發出低沈又緩慢的「呀」的聲響。屋子裡漆黑一片。靠近門的地方,看得見凹凸不平的石板地面,裡面一點鋪的是木板。進門左手邊是一張和門板一樣殘破的木桌,上面放了一支沒有燒儘的蠟燭,兩瓶啤酒,還有一本皺巴巴的留言簿,翻開一看,啤酒是兩個月前有人留下的。打開木板窗,光線勉為其難地透了進來,這才讓人看清楚屋子內部的構造。離門最近的是一張單人床,再往裡去,左右兩個仍然昏暗的角落裡,分別放置了兩張上下鋪的高架床,這個屋子足可以留宿五個人。臨門的木桌子後面,像是一個灶臺,但已經塌成一堆亂石,它的上面是彎向屋外的煙囪,坍塌前也許是一個壁爐吧。靠著山的半個屋子是掏空造出來的,低矮的穹窿屋頂讓這整個屋子看起來像是一個墓穴,尤其是藏著半張高架床的黑暗拐角,令人不敢靠前。這時候我才發現,進門的右手邊還有一個低矮的小門,被一塊破舊的簾子遮住了。輕輕掀開簾子一角,定睛看了看,原來那是一間完全廢棄了的空房,地上散落著石塊瓦片還有分不清形狀的碎屑。我把簾子重新拉嚴實,就當它並不存在。
下午兩點多,時間還早,我重新坐回到視野開闊的木桌椅上,在本子上寫字,等待雨信。深谷對面的山頭上烏雲低垂了下來,大風將它們一會兒攏過山頂的曲線,一會兒又騰向天空。山谷盡頭,白雪覆蓋的那幾個山頭也開始浸入了濃霧之中。一滴雨及時地印在木桌子上,留下更深一點的木頭的色澤,繼而再一滴、兩滴、五六滴……本子上的字跡還未完全干,有些已經被雨滴溫柔地擊中,墨色四散開來。
站在屋簷下,聽到雨聲變得稀裡嘩啦響,打在屋頂上,從屋簷掛起水簾,砸向地面上的一排小坑窪。過了許久,對面的高山完全被大雨一幕幕地遮起來了,山的形狀在低沉的光影中變得含糊不清。我馬上穿起防雨外套,戴上帽子,把相機抱在懷裡衝進雨中去拍對面的山崖,為避開屋前樹葉的遮擋,我大步掠過屋前的坦地,往崖邊爬下去,與瘋狂的雨水和茂密的草叢糾成一團。
大雨模糊了山林,只剩下巨大的山的輪廓,甚至山脊線也要被抹去了。相機取景框已經徹底看不清了,鏡頭也一片朦朧,一擦拭完就馬上拍。眼睛都要看不清風景的時候,遠處的半天中忽然又露出一抹山容。我和相機都濕透了,在我的手指快要凍得不會按快門的時候,快門因為進水也按不下去了。大顆的雨珠連續不斷地打在樹葉上、樹枝上、草地上,碎成細小的水珠再濺出來,我感覺自己激游在層次分明的雨山圖卷之中。
衝回到屋子裡,迅速在浸濕之前取下膠片捲包起來,然後脫下川流不息的外衣,扯掉沼澤一般的褲子,拔出水泥一樣的登山鞋。壁爐石堆邊有一些不知多久前沒有燒盡的柴頭,儘管並不乾燥,我還是努力地用廢紙和蠟燭生了一個小火堆,關上門窗,讓生澀的柴火冒出大把大把的青煙,把整個屋子熏成一團人間煙火。
這幾根柴頭燒了不到一個小時,衣物遠未烤乾,已經無物可燒了。四點半,山谷騰起了雲霧,雨似乎停了。出門一看,陽光照耀了整個山谷,嵐氣奔走……這樣的景緻,不就是我故鄉的山村,那個小小的世界變幻無窮的風景之一嗎?夏天的雨後,山嵐從村口的竹林之上生出來,飄過前山,又赴向對面山嶺要與另一團匯合,但在半途中就漸漸地稀薄淡隱下去。人們呆在屋子裡,對屋外雲氣的變幻視若無睹,只感覺在屋子裡,空氣變得清涼,或者有些寒意。黃昏之時,家家戶戶的灶臺後面一定有個熱愛燒火的人,蹲在那裡專心致志地盯著旺盛的柴火出神。燒著火,白天的光暈就讓給火了。炊煙與黛青的晚色相比,總是顯得柔白,哪怕夜晚漸深,炊煙依然可辨。煙散了,黑夜就來了。而我此時卻在遙遠的大陸彼端,在一座廢墟上忽然懷鄉起來。人們幾乎已經遺忘一百年前有這個山村的存在,這裡也再無燒火做飯,劈柴抽菸,喝酒憂愁的人。
我想要不要離開這個黯淡的地方,去更遠處的那個或許是真正的木屋,走路三四個小時就到得了,一個人飛快地走應該是來得及的。正考慮著,就發現了積雨雲又從山的另一邊悄然翻過來了。
大雨中山的巨大輪廓,「阿爾卑斯」系列,2014年
我折回昏暗的屋子,站在門口。走不了了,此時此地,這就是我短暫的棲所吧,我也不必再趕路。
在這個半廢墟的洞穴里,地面上有許多細碎的樹枝、殘葉、石灰塊,以及種種打碎了形狀卻還沒有成為塵土的東西。這些大自然的無用物,正要變成泥土去滋養它物的半途中被帶進了這裡,困在了輪迴的路上,停滯在這種非生非死的狀態。我把它們撿了撿,能用的有一小把,堆在剛才的火堆邊。掃了掃單人床上的灰塊和塵土,我攤開了背包和睡袋,這就安頓好了。趁著天還亮著,我決定出門走走。
路邊的野草野花飽蘸了雨水,雙腳遊走其中,輕輕一劃,便是一場大雨。很快我的褲子和鞋子又泡在水中了。我一邊走,一邊與對面的山林相望。一面山林,就是一幅可以凝視一生的圖畫。每一株松樹就是一個含蓄的筆觸,與其它的每一個筆觸一起,縝密地生在峻峭的山體上,雄渾的高山就長出了細膩的肌膚來。對坐了許久,我又划着小徑上的水珠,在漸漸來臨的細雨中走回了我的小屋。
一個人住在這個屋子裡,首先要驅趕的就是黑暗。然而我已經沒有蠟燭,也沒有柴火了。定了定眼神,我在黑乎乎的灶臺角落裡居然搜出三四根細柴,儘管十分潮濕,但聊勝於無,一會兒就能生起火來,這麼著就可以安心進入夜晚了,我想。重新攏了攏先前的火堆,隨手撿了三兩塊石頭搭起了一個小小的灶臺,把細柴的一端砸成柴糊糊,劃燃了火柴就耐心燒將起來。小火屎怯生生的,眼見著要燒起來,卻瞬間又滅了。外面的雨變大了,天色昏暗,我體會到我們的祖先刀耕火種的艱辛。

石頭下面奔騰的溪流,「阿爾卑斯」系列,2014年
生火,是人之成為人的第一項本領吧!微弱跳動的火光,照亮一小塊從未暴露過的黑暗角落,這就足以讓人產生驅逐茫茫黑暗的雄心。我全神貫注地輕輕吹拂木柴之間的星火。無法計算過了多久,就在那一瞬間,毫無預兆地,一團火焰優雅地生起來了。木柴一端滋滋滋地吐著水珠,青煙四散開,我感覺完全地活在了文明最初的氣味中。脫下的衣物貼在火堆邊的石頭上,飽蘸了雨水的鞋子幾乎埋進了火堆,但最終還是沒有烤乾。我光著身子坐在一塊石頭上細心照料著火堆,眼見著火光慢慢黯淡下去,身前的溫暖也漸漸被寒冷侵佔。青煙還未散去,黑夜也許已經來了。 最後一根火苗已然熄滅,我躡腳踩著冰冷的石塊走到床邊,鑽進睡袋,把拉鏈拉到腦袋上,又把袋口收緊,整個人成了一團蠶繭。我的腳伸向恐懼源頭的幽暗拐角,頭朝著門。鑽在狹小的睡袋中,偶爾聽見火堆那邊發出微小的爆裂聲,我每次都相信火又燒起來了,伸出手鬆開袋口,探出頭來,朝著火堆盯著看許久,地上的炭火卻每一次都比先前更加黯淡下去了。 我摘下手錶放在床頭,沒能看清是幾點鐘。精確失去了意義。唯一可以依靠的是大自然的光。雨山中的光,在漸漸褪去與重新到來之間,就是漫長得無法計量的黑夜。我等待黑夜的降臨,感受昏暗再昏暗一點。不知過了多久,一切彷彿停滯了好一會兒,我被寒冷激活了一下。此時要是穿上衣服睡該有多好啊,我幾乎忘記了它們還是濕噠噠地晾在石頭上這件事。背包裡面只有一雙襪子是乾的了,一度想要把它們翻出來穿上的意念,身體始終無法戰勝緩緩沉下的睡意。真正睡去之前的最後一刻,我再次探出頭來,小屋裡已經濃黑得不見五指,我感覺自己與無邊無形的雨山融為一體了。 沉睡間,有幾個人推開了門,在屋子裡隨意地坐下來,輕聲說話,吃東西,還生了一堆火。火苗不大,但足夠伴隨黑夜緩慢的流逝,整個屋子也都被照亮了。他們說什麼我始終沒有聽清,不敢起身打攪,也沒有睜開眼睛,卻看到他們在牆上、地面上漸漸地隱去了。我想我是借了他們的暖意才睡著的。再次睜開眼,天已經亮了。鼓了鼓氣下了床,一拉開門,但見一片大霧。霧中還有牛毛般的雨。山也完全看不見了,只隱約見到屋前的樹影,彷彿一早問好的鄰居。我回到屋子裡,花了一些時間寫下如上的文字,留下了所有的食物在桌子上,依依不捨地出門下山。走了十幾步,回頭一看,屋子已經消失在山霧中了。 2014年7月於阿爾卑斯山中