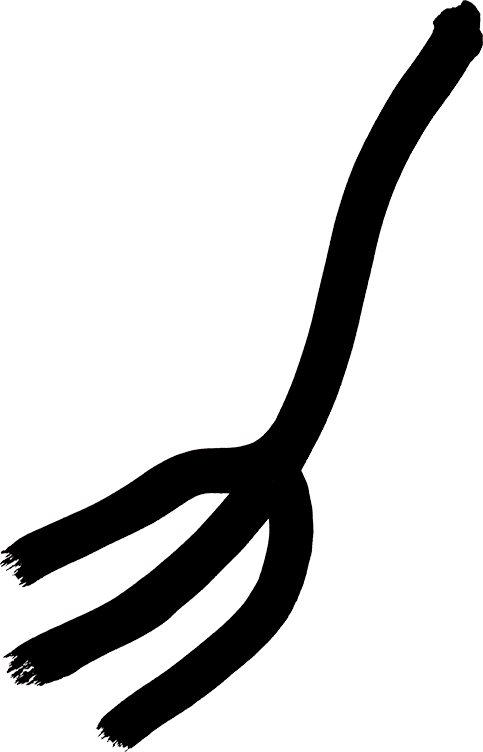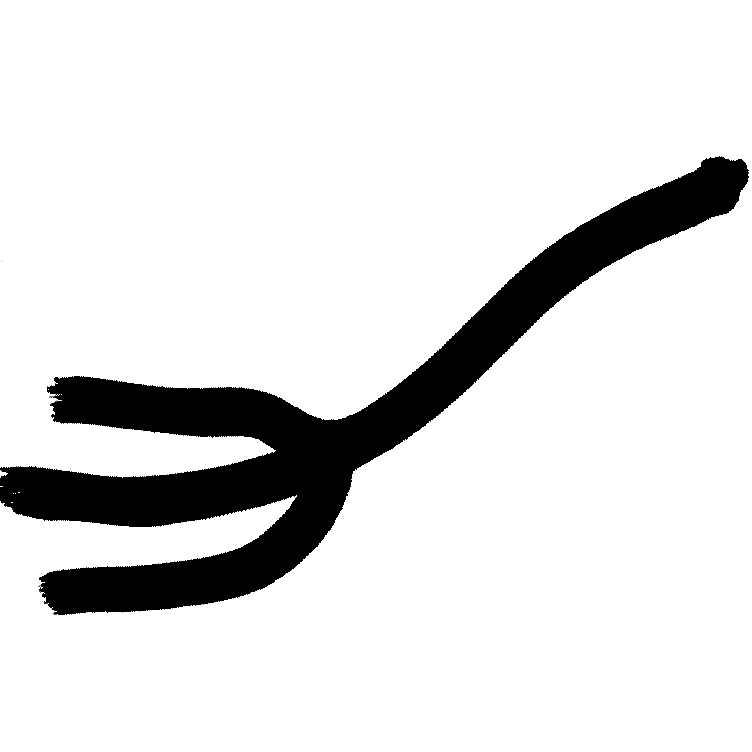14 Jul 生死的分界

去往Font froide的山路,「阿爾卑斯」系列,2012年
一座山爬兩次以上,就會覺得這是自己的山。開始分辨每一條小徑的形狀,對山勢升攀、緩延、陡降之變化也有了明確的感知,走在這個巨人的身體上,偶爾抄個小道,也不再害怕危險的存在。走進山腳茂密的森林中,光忽然幽暗,而在穿出高大的松林的瞬間,世界又重新明亮起來。小路不遠處,森林遮蔽著山谷裡咆哮的溪流,沿途伴隨著爬山的人。當水聲漸漸遠去,消失在鬆脆的石塊底下的時候,我就站在了冰泉山(Font froide)的真正開始攀爬的地方。
兩年前的七月初,我從阿爾卑斯山靠近意大利邊境的那一邊,上山下山騎了一百多公里來到冰泉山下的小村莊。一整天的奔走,抵達山村的黃昏時我已經搖搖欲墜。在村口看到了我的朋友皓嵐的母親和他的幾個摯友。一年前他獨自一人消失在這座山中。為了這個週年紀念,我們一起爬山。
艾坎山區(Ecrins)是阿爾卑斯西部山脈中平均海拔最高的一片,主要的山峰都在三千到四千米的高度。有時候在山谷,一抬頭就能望見冰川積雪的山頂,然而要抵達這個就在眼前的目標,要走上大半天的路。山體之龐大,猶如一面洪鐘重重地扣在大地上。穿過森林,走上陡峭的岩石碎塊,有些地方甚至要四肢並用方能爬上去。每上升一點,回頭就能看見身後的高山再顯露出一層。極遠處正在下雨,雨陣漫過群山,襲來陣陣寒意。我和皓嵐的家人朋友,像是一列螞蟻,低著頭斜在亂石的山道上緩緩前進,每個人都若有所思。
為什麼一個人來爬這座山?一年前的那一天,不像今日這樣陰沉,天空完全的晴朗。路邊的小野花,該是見證過他的身影。山上的積雪,也曾覆蓋他的腳步。人為什麼爬山?山神隨時都會不經意間抹去一個生命,甚至毫無蹤跡。低著頭緩緩地攀爬,誰都沒有答案。只有粗粗的喘氣,散發著熱量的身體和冰冷的風,在一步又一步的移動中獲得一種溫度上的平衡。只要停下來一會兒,身體中小小的一團火就會被寒冷的山氣漸漸吹滅。
相比這腳下的洪鐘,更沉重的乃是每一個爬山者自己的身軀。每攀爬一步,都在克服一點肉身的沉重。從前我以為,爬山就是在反抗肉身,用腳步來一點點脫離喧鬧,跳出三界外,接近無限的天空和光明。站在高山頂上,跳一步都要小心翼翼,生怕一不小心就墜落到最初的低谷,在墜落中化為塵埃。人,永遠也不能抵達天空和光明。可這樣失落的旅途,還是吸引著人們不停地花費如此艱辛向上攀爬,即便明白山頂除了“空”,或許再有一陣陣風吹來,其實什麽都沒有。
當我第一次來到這個空空的山頂,爬到陡峭的岩石上,往峭壁下看,想像一個人的身體墜落下去,受石塊的撞擊,動物的爭奪,日落之後徹底消失在寒冷的黑夜中,與泥土岩石,小花小草,動物的痕跡不辨彼此。我不由的感覺到這是一種奇特的死亡,一個卑微的軀體,包括它所包藏的感知疼痛和歡愉的神經,在短短的時間內就化作了不生不滅的狀態,譬如雲中鳥,一去無蹤跡。
在山頂呼嘯的風中,誰都沒有多說話。放了一束鮮花在石頭堆上,每個人好像都陷入了完全的沉默。皓嵐的母親,站在群山的中央,在這一列人的中間,看著腳下空空的山谷。我無法揣度她心裡翻湧的情感。在廣袤無垠的寒冷天地中,那小小的一團火焰應是在最炙烈地燃燒著。那該是飽含愛意的母親擁抱著孩子的溫度。然而她站在那裡,獨單一人。
我們陸陸續續地爬過去,和她深深地擁抱,代替她的孩子,在這群山之巔接受一個母親的愛和思念。
下山的時候大家忽然都輕鬆起來,臉上都露出了一種滿足,在往下走了一段路之後,攤開揹包裡面的食物,切著火腿和奶酪,夾著麵包在寒風中哆哆嗦嗦地吃著,大家的臉上,分明露出來一種穿越生死的過後的輕鬆,甚至有些愉悅起來。

臨近山頂的冰川,「阿爾卑斯」系列,2014年

埡口,「阿爾卑斯」系列,2012年
再兩年以後,皓嵐的家人為他在山下的村子里修建了一個小小的墳墓。山村很少有人住了,這裡也不是我們任何一個人的故鄉,自從他出生的那年起,那個荒廢的墓園就再也沒有新墳安置進來。幾塊東倒西歪的石頭上,有些長著青苔,在除不盡的野花野草中還能看見幾個被遺忘的名字。當地的一個雕塑家從山穀裡搬來一塊岩石,安插在墓園的角落裡,不經雕琢地為他做了一個樸素的墓碑,只在岩石最上面,安放了一個很小的雕塑,半個拇指大的小人兒,背對著墓園,正在走向岩石寓意著的山頂。兩年前在山頂的空望,現在變成了在山下,在人間裡,看看這個小小的想像的背影。
這一次,登山的隊伍只剩下了我們四五個年輕人。草木深沉,在森林中大家就已經迷了路,竟然走進了乾涸的山谷中。我憑著照片中的印象,找到拍照片等待過觀察過的地方,總算找到原先走過的路。而在乾燥的石塊上,很難分辨出人的腳步印出的羊腸小徑,越接近山頂,小路越是隱沒,如果再注意一些,通往山頂的路不知何時就沒有了。接近埡口的那一段路被積雪完全覆蓋,每個人都在厚厚的雪上如履薄冰地探路,兩年前走過的痕跡已經全然消失,最後以接近攀岩的方式翻到了尖聳的山脊。
在尖聳的山脊上,我們小心翼翼地挪動著身子向四周探望,好像在確認就是這個地方。但又感覺這裡比之前更加陡峭了。不見了燈火照耀下日夜搜尋的焦灼,不見了浮現在腦海中各種慘象引來的悲痛,不見了一次又一次落空的希望,不見了默默接受的荒誕,也不見了鮮花堆疊的告別,我們來到了到處都是陡然下落的埡口。就連搜救犬一路嗅著氣息確認的那個埡口我們也找不到了。我們也只能自我安慰道,身前這個,就是他墜落的地方。
躡著身子附著在峭壁的邊緣,看著遠處的冰川,有些山頂完完全全被覆蓋在似雲似霧的一團寒氣中,這完全是另一個世界。而眼前這個巨大的一落到底的山谷中,沒有亂石,也沒有雜樹可以遮埋一具軀體。他就是這樣消失了。好像走在山脊的任何一處,像現在這樣,向對面遠處的雪山觀望,在凝視中,情不自禁地往前邁開一步──人,經過一路克服沉重肉身的攀爬,在人間的邊緣,往外踏出了一步,便倏地遁形了。
這個明顯的分界之前,山路有意把人引向別處,分散著也阻擋著人們來到這個邊界。當你清醒地、幾乎百折不撓地爬到這個懸崖邊,才發現自己是在兩個世界的狹小的縫隙中。這兩個世界,是冷和熱,是生和熟,是虛與實,是無情與癡情,是永恆與剎那。
無路可走啊!
俯身下去,那裡連一個腳印都看不到。里爾克說: « Où nul chemin n’était tracé, nous avons volé. L’arc en notre esprit est encore marqué. » 無路之地,我們飛過。心靈之虹尚存。
而我們來爬山,走過他最後的陡峭的路,體驗他最後為人的體驗,卻無法感受他離開這個世界的那一瞬間。在山頂的崖壁上,眾人的沉默就像在說:再見皓嵐,只能送你到這兒了。眼前這個空谷之後的世界,視野無法窮盡的高山和冰川,若不是漫飛,又豈能到達?
我們的那個人間,在身後的山腳下,那兒有一片森林,森林保護著它的溫暖,蔭庇著它的雞鳴犬吠。下山的時候,我看見冰川腳下的不知何處跑出來一頭巖羚羊。它敏捷的四肢悄無聲息地在陡峭的岩石上跳躍。我站在莽荒之間,遠遠地注視著它的身影。它穿過大塊的岩石,穿過小樹叢,穿過乾涸的小溪,漸漸與山川的顏色融為一體。它正在我已經分辨不清的顏色里,肆無忌憚地奔跑向我們的人間。
2014年七月於阿爾卑斯山